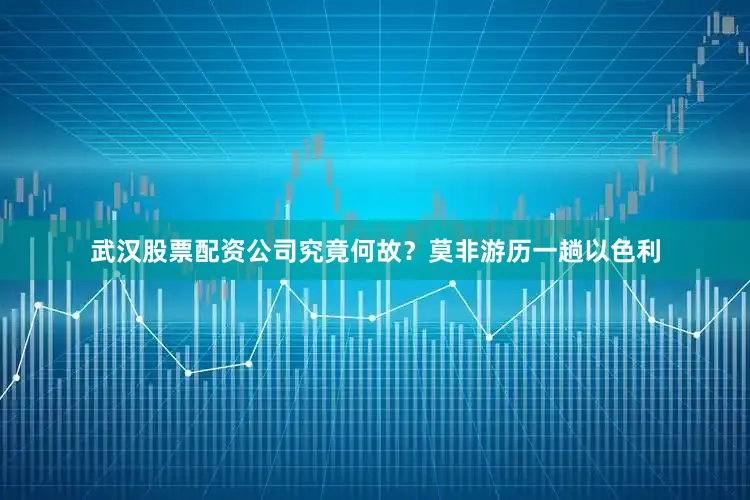当洋传教士罗孝全瞧见东王杨秀清上演“天父降临”那一幕,简直被震惊得不行,心想这上帝居然还能下凡尘,而且还“文绉绉”地讲起中国话来,难道是我们认知的上帝不对头?还是说咱俩拜的不是同一个上帝啊?
早在唐朝时期,基督教就试着在东方探探路。到了明末清初,虽然有像利玛窦、汤若望这样的耶稣会士在中国努力传教,但效果并不明显。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的传教士们带着他们的商品,不远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成群结队地开始大范围传播他们的信仰,可结果依然不怎么好。

最终,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还得靠中国人来解决,洪秀全帮他们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太平天国的影响力,让在华的各国传教士都感到十分震惊。
传教士们都觉得,现在是在中国推广基督教的大好时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除了少数反对的声音,大部分人都是持赞成和给予鼓励的态度。
说起对洪秀全有直接了解,而且对太平天国最兴奋激动的,大概得数罗孝全了。
罗孝全是个美国人,他出生在1802年,年纪比洪秀全足足大了十二岁。
罗孝全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开创了好多先河:他是头一个到香港传福音的外国传教士,也是头一个在香港盖教堂的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教浸信会的开办人,“罗孝全基金与中国教传会”的首任负责人,更是第一个和洪秀全见面的外国传道人。

罗孝全因为工作努力、坚持不懈并且名声在外,在中国书写了自己的一段精彩故事。
1847年,洪秀全写好了他的革命想法后,感觉自己在宗教方面的了解还是不够扎实,因为他从梁发那里学到的那点基督教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毕竟梁发也不是正宗的传教士。
正当洪秀全满心想要提升自己学识的时候,周道行为他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靠着周道行的帮助,洪秀全和洪仁玕一起来到了广州,目的是拜访已经在那里传教的罗孝全,希望能够得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
这时候的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的时候碰了个大钉子,正处在刚开始打拼的难关里,想必心里头特别憋屈和郁闷。
人要是走霉运,连狗都不愿意靠近。洪秀全心里头苦得很,脸上也绷着个脸,罗孝全看他特别不顺眼。
两个人能不能处得来,关键看初次见面时的感觉,这在心理学上叫首因效应。洪秀全第一次给人感觉不太好,但他还是满怀希望地去要求受洗,没想到被罗孝全毫不留情地给回绝了。

罗孝全后来自己回忆说,他之所以没答应洪秀全,不光是因为第一感觉不太好,还因为另外两个很关键的因素。
头一个缘由,就是信息交流不对称,中西方在文化交流上存在隔阂。
洪秀全跟罗孝全仔仔细细地讲了自己考试落榜后,在生病时做的那个既像真又像假的白日梦,心里盼着这位懂行的人能对他刮目相看。
洪秀全心里挺不是滋味,因为罗孝全的态度大大打击了他的自尊和骄傲。罗孝全非但没有像其他拜上帝教信徒那样对洪秀全充满敬意,反而给了他一个让人摸不清头脑的眼神,还愣在原地,一脸惊讶。
罗孝全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并不多,在那个心理学还没成气候的年代,洪秀全的报告让他听得一头雾水,这也不能全怪他。
洪秀全讲述的梦境并未如愿以偿地产生影响,反倒让罗孝全一眼就看穿:洪秀全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不难看出,罗孝全的感觉没错,洪秀全确实不是个真正的基督徒。
比如说,他声称耶稣是上帝的第一个孩子,而他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孩子,这种说法恐怕会让基督教信众气得不行。

洪秀全对宗教的了解不够深入,这是罗孝全不太瞧得上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的又一个缘由。
洪秀全虽然没被西方传教士直接迎进上帝的大门,但他没生气走人。相反,他和弟子洪仁玕一起,在广州的礼拜堂里默默待了四个月。他们低调说话,但学习劲头十足,不仅认真了解了基督教的仪式规矩,还细读了基督教的新手必备书——《旧约》和《新约》。
洪秀全以非正式学生的身份,临时突击学习了基督教的相关知识后,和洪仁玕一起回到了他们的老家广东花县。

洪秀全和罗孝全分开后,他俩大概都没料到,前面等着他们的,会是那么出人意料、既惊险又让人惊喜的事情!
洪秀全高兴的是,紫荆山的拜上帝教徒人数大涨的好消息。
罗孝全收到的意外好消息,是由之前和洪秀全一起来学艺的洪仁玕告诉他的。
洪仁玕是洪秀全早期的重要伙伴之一,他参与了金田起义,但没多久就和太平天国队伍走散了。到了1852年,洪仁玕挺倒霉地被清军给抓住了,不过他后来找机会逃了出来,并在那年春天费了好大劲来到了香港。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里的老将,也是拜上帝教最早的信徒之一,虽然人在香港,但心里总想着太平天国。回想起以前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他常常望着西方,怀念过去的时光,梦想着能再次回到天国。
心里装着感情,话儿就从心底冒出来。洪仁玕把想念说了出来,然后由瑞士巴色会的传教士韩山文把这些话写成了《太平天国的故事》。
韩山文把这本书递给了罗孝全。罗孝全翻开一看,大吃一惊。天呐!这不就是五年前我狠心拒绝的那个东方信徒洪秀全吗?
听说洪秀全没被选上后,居然自己开了家大铺子,罗孝全后悔得要命!他反复埋怨自己,以前怎么就没看出那是个厉害人物,还狠心地把人家给赶走了呢?

罗孝全对自己过去像洪水冲垮龙王庙那样做错事感到懊悔,为了不让别人再走弯路,他认真地给全英国的朋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里,他劝大家别帮着清政府去对付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他特别强调,洪秀全不仅仅是要和朝廷对着干,更重要的是,他在为宗教的自由而战斗!

罗孝全说,谁要是和太平天国作对,他肯定会跟那人彻底翻脸。
罗孝全心里不光惦记着同胞和同行们,还莫名地对洪秀全有点不放心:洪秀全这家伙,当年没学到我的真本事,要是他搞的拜上帝教走偏了路,惹出大乱子,那可咋整啊?
听说太平天国把上帝崇拜在天京搞得轰轰烈烈,罗孝全心里头那股子急切再也憋不住了。他急着想给洪秀全上一课,没想到好运降临,被一个骗子帮了大忙,收到了一份假邀请信。
罗孝全被骗子耍得又激动又开心!没想到邀请他的人竟是洪秀全,说是要请他去天京讲大课,给大伙儿补上以前落下的学问。
被瞒在鼓里的罗孝全,觉得自己再也忍不住要发疯了,连忙向在上海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马沙利递上了要求去天京的申请。
说起来也怪,就算罗孝全了解了实际情况,他可能还是会心甘情愿被骗,甚至可能还会感激那个骗子,因为这让他有了机会向上面提出申请。
信寄出去以后,罗孝全觉得在广州等回信太浪费时间了,就自己直接出发去了上海,打算见到马沙利,当面拿到他的同意后,就立刻动身去天京。

但没想到,罗孝全因此特别苦恼。马沙利告诉他,按照条约规定和法律条款,他不能前往。还警告罗孝全,要是你偷偷跑去天京,我就把你直接送回家乡!再不听话,我可真要把你绞杀了,信不信?
马沙用嘲笑的眼神看着吓得不行、失望透顶的罗孝全离开后,转头对着美国商人小侯尔德,把罗孝全好一顿数落:“这家伙真是个书虫!还写什么报告,他自己去不就完了嘛!”
当领导也有领导的苦恼!有些事,你不跟领导说一声就做了,领导可能也就装作没看见,事情过了就过了,大家都没事;但你若要是特地跟领导报备,这事儿反而可能泡汤,领导只能告诉你不行,不然以后真出了问题,领导也得跟着倒霉啊!
小侯尔德是个做生意的,很会琢磨上司的心思,马上就把话转告给了罗孝全。
罗孝全没顾得上琢磨自己在官场上的失误,一门心思扑在了策划去天京的事情上。但之后的一系列经历,让他彻底明白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罗孝全多次尝试前往天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直到1860年,他才终于圆了多年的梦想,见到了洪秀全。
当洋传教士罗孝全瞧见东王杨秀清扮演天神下凡那会儿,他真是大吃一惊,心想上帝居然还能亲自下凡,还满口之乎者也地说着中国话。这让他犯嘀咕了:难道是我们信仰的上帝不对头?还是说咱俩拜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上帝?
咱们换个逗趣的说法:说不定杨秀清那场秀,是上帝想给那些洋教士露一手,展示下他的全能才艺呢!毕竟,上帝的想法和做法,哪是我们这些凡人能轻易琢磨透的!

【洋兄弟雾里看花】
牧师讲道义,商人看利益。传教的哥们儿因为对传播宗教特别上心,所以他们在意的是太平天国有没有搞错上帝的教导。而那些外国商人呢,他们琢磨的是太平天国这么一闹,是能给自己带来赚钱的好机会,还是要让自己破费倒霉了。
赚钱的好时机,突然间就到了眼前。太平天国的水军攻打南京,可把江苏巡抚杨文定急坏了,他一边忙着逃跑,一边又赶紧让上海道台吴健章去向外国人求帮忙。
吴健章还有个别名叫吴爽,他以前在洋行工作过。杨文定想利用他和洋人之间的特别交情,让他去说服上海的英法领事,派些兵船来救援南京。
但上海英法领事对此根本不理睬,吴健章没办法,只好去找那些普通的洋人,和他们做起了买卖军火的生意。
吴健章费了好大劲,终于弄到了两艘帆船,一艘取名叫财政长官号,另一艘叫羚羊号。这两艘其实是货船,只能用来装载武器和兵士。此外,他还每月花五万块,从美国的旗昌洋行租了艘老旧的船,并且找了一队葡萄牙的武装小船来帮忙。

吴健章带着他那支“国际海军大队”逆流而上,想挡住太平天国水军往东的势头。没想到,旗昌洋行租来的大船刚到镇江口外面就无奈地搁浅了,而葡萄牙的小船也在镇江被罗大纲带的水军打得落花流水。
吴健章之所以栽跟头,不是因为西方的海军不堪一击,而是因为他买的都是次品货。杨文定想靠洋人来救南京,是因为鸦片战争时,中国官员已经领教过洋人海军的强大——船大炮猛。但多数商人都有大志向,看得远,不稀罕吴健章那点儿小便宜。他们不愿太早暴露实力,也不想急匆匆地帮清政府去打太平军。
说实话,那些外国商人们心里挺纠结的。一方面,他们怕这样拖下去,社会越来越乱,他们不远万里从老家运来的那些工业品,在中国就更难卖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思想上有点沾亲带故,所以他们对以后能和太平天国联手挺有信心,还做着发大财的美梦呢。
外商们对现在的买卖挺不高兴的。自打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的商品在中国卖得并不好。虽然关税已经低得破了世界贸易的纪录,但因为他们只能在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这五个地方做生意,再加上咱们中国自己种地的小农经济特别能扛,所以那些洋布洋纱在中国的销量,根本没有达到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火爆。

外国商人们心里也明白,自家人好商量,他们琢磨着要是太平天国把清政府给推翻了,洪秀全念在大家都是信上帝的同门的份上,说不定能给比清政府更宽松的贸易好处呢。
咱们再聊聊吴健章请求援助这事儿,其实挺能说明西方政府的态度。英国在上海的领事阿礼国,他没有直接答应吴健章向英国求助的事儿,而是把问题往上推,说要是想商量派船去南京救援,最好还是让两江总督直接找英国的公使,也就是香港的总督文翰先生去谈。
吴健章没办法,只能再次找文翰帮忙,但文翰一点都没拐弯抹角,直接说:“不行!你们自己搞定吧,我可不想掺和这事。”
文翰派了翻译官密迪乐去找吴健章,跟他说他们会照看英国人的安危和财产,但要是说出兵帮忙,那门儿都没有!
吴健章对英国外交官的态度感到一头雾水,没办法之下,他只好去找商人帮忙,东拼西凑组建了之前提到的那支“国际海军队伍”,这样总算是给上司杨文定有了个交代。

英国的大使文翰没答应清朝地方官的请求,这背后有好多复杂的原因。在弄清楚两件事情之前,他不会随便站边支持哪一方。
外交就是国家间为了好处而进行的较量。如今太平天国有了自己的京城,算是个正经国家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跟清政府平起平坐甚至把它打败。这样一来,英国现在也没必要急着帮清政府对付它了。
清政府看太平天国,就像是眼中钉肉中刺,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强盗;而外国人呢,他们不太在乎名头响不响,更看重的是谁拳头硬,说白了就是谁的战斗力强。文翰为了在外交上占得先机,打算先去摸摸太平天国的底细。

太平军不仅让清政府晕头转向,也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到底是清政府能赢,还是那些被清政府视为黑帮的势力会胜出。再说,哪个新政府上台前,没被老政府说成是黑社会呢?
太平军攻占镇江和扬州后,文翰觉得不能再拖延了,他派密迪乐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探探太平天国的虚实,评估一下太平军的实力。
密迪乐从上海启程,路过苏州和常州,最后抵达丹阳,隔天他又回到了上海。这次旅行,密迪乐弄明白了一件事:太平军真的信基督教,跟咱们算是同宗啊!

后来,英国的文翰公使抵达南京,他派密迪乐带着正式的外交文件去见了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密迪乐先表明了英国保持中立,不帮任何一方的立场,接着就问起了太平天国对西方国家的看法,还有他们会不会去攻打上海。这其实是文翰跑到南京来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们特别想知道的第二个事儿。
密迪乐又聊起了接待英国大使的礼节事儿。北王韦昌辉没直接回答,但对他挺客气,说想和英国人交朋友,保持好关系,还劝他们别帮着清军。
后来,太平天国对文翰说,他们的天王就像是各国的老大,凡是来拜见他的,外交上的规矩礼仪都得做足,怎么能这么随便呢?
文翰回想起马戈尔尼在乾隆时期体验到的清朝那种高傲自大,这和太平天国的态度有点像。这让他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他吩咐密迪乐把太平天国的信件退回去,还附上了一份1842年和清政府签的《南京条约》复印件,好让太平天国看看清政府曾经受过的屈辱。
心情不好的密迪乐,因为任务没完成,第二天就碰到了天京那边派来的使者。使者说,东王杨秀清对昨天文件里的语气觉得不好意思。密迪乐又跟使者说了英国不站边的事儿。更让密迪乐惊喜的是,使者还告诉他,东王杨秀清邀请公使文翰第二天上岸去见面呢。
文翰吃过亏,不想再因为仪式上的小差错惹麻烦,所以就礼貌地回绝了东王的邀请。他还在书面回复里一再强调自己是中立的,绝不会给清政府提供任何帮助,让东王可以完全放心。
东王于是提笔回了封信,信里头先是对天父和天王好一顿夸赞,接着热情邀请各国的朋友们来天京逛逛,或是来做买卖。只要是愿意支持天国的,我们都张开双臂欢迎。
文翰读完信,心想东王说的话也太夸张了点,怎么好像东方上帝才是正主儿,把咱们都晾一边了?文翰心里嘀咕着,又一次强调,英国人在中国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是碰不得的。要不然,十年前清政府在南京下关签的那个《南京条约》的事儿,可能又得再来一遍,到时候就得多个《天京条约》了。

文翰到天京走一趟,是替英国政府提前探探太平天国这个“黑马”的底细,就像是下注前先瞅瞅对手的实力,或者结盟前摸摸对方的底,免得吃了亏。太平天国老说他们是洋兄弟,但那些外国人对着他们崇拜的神奇东方上帝,还有攻下天京的能耐,感觉就像雾里看花一样,完全摸不着头脑。
说实话,杨秀清他们刚开始跟外国人打交道时,对这些新来的洋朋友,还有西方上帝管着的老外们,都是雾里看花,看不真切。但话说回来,能搞清楚这些洋朋友不会跟咱们自己人动手,也算是太平天国眼下能乐呵乐呵的一件好事了。
那些洋大佬们虽然表面上没啥动静,但眼睛可一直盯着太平天国呢。他们心里最挂念的两件事儿是:一来,中国这场自个儿打自个儿的仗,会不会挡了他们的财路;二来,太平军要是打下了上海边上的镇江和扬州,会不会接着往东冲,直接打上海的主意。

因此,文翰对吴健章说中国内部事务他不插手,但心里却急着搞起秘密外交活动。与此同时,那些在上海的各国外交人员也都没闲着。
那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是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个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上海的外交人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他们还弄了个叫上海租界防御委员会的组织,招兵买马,进行训练,还建起了防御设施。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备中国人反击时,能保住他们从清朝政府那儿强占的地盘。
【致命的软肋】
老外这种忧虑,挺有道理的,按常理来说确实该这样想。太平天国占领了镇江和扬州,要是他们继续顺着水流往下打,上海就危险了;要是他们快速往南进攻,苏州和杭州也守不住。
都说好地方要数苏杭,上海自开放后,经济飞快上涨。拿下上海和苏杭,不光能捞到大把好处,还能让清政府钱包紧张。再说,那时候上海和苏杭已经人心惶惶。苏南的清军呢,都被陆建瀛大人调走去守江宁,拦着太平军了,苏南那边几乎没啥兵力守着。
太平天国攻占江宁后,杭州将军有凤和副都统巴彦岱,后来有凤还调去了福州当将军,他俩一块儿给咸丰皇帝发急信:咱们这儿只有一千六百旗兵和两千绿营兵,这局面可咋收拾啊?

在杭州,浙江的头头黄宗义办公的地方,手下正规军和民兵加起来才六千人,他也忍不住跟咸丰皇帝倒起了苦水。
大臣们在抱怨,说白了就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来想让咸丰皇帝多派些兵马,二来想提前撇清关系,免得日后追究责任。咱们手里的这点人马,哪里够跟那些反贼大军对抗啊?
老外也慌了神,这才有了文翰出去打探消息,还有上海租界里头的军队忙活起来。
但其实,他们白操心了。太平天国把都城定在天京后,就没再继续攻打别处,反而开始转守为安,想着怎么防守了。
世上的事儿,到处都藏着简单的对立统一,南京就像个大门紧闭的院子,进去的人都不想离开。在院子被攻破前,外面的太平军拼命往里冲,里面的清军死命守着;可院子一旦被攻破,原先冲进去的太平军就得开始守着,而外面的清军反倒变成了攻打的一方。
城市易主之后,打仗的两边攻防形势也无奈地调了个个儿。
太平军已经攻下了城池,接下来怎么守住这座城,就成了他们最紧迫的事情。
拿下镇江和扬州这两座城市,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开始守护城池的第一步。

太平军有个特别的打仗方法,就是喜欢分开兵力守不同的城。他们在道州时,就分了一些兵去占领南边的江华和永明两城,这样和道州就形成了互相支援的局面,也为以后突围做了准备。到了郴州,太平军又用同样的方法,攻下了郴州北边的永兴,来保护郴州,作为继续往北打的基础。后来,洪、杨的主力部队到了郴州,就让西王萧朝贵带着精兵突然攻打长沙,这时候他们的战术就变了,变成了“城里守住,城外再攻城”的办法。这个办法后来还成了太平天国打仗的主要思路。
这种策略就像这样:站稳脚跟,一只手挡住攻击,另一只手出击!
攻下南京后,再往东拿下镇江和扬州,这其实是又一次使用了分散兵力保卫城市的策略。用现在的话说,就像是先占领周边的小城市,再来保护大城市的安全。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太平天国把都城定在天京才没多久,也就二十来天吧,就有两位大官开始死死盯着太平军了。就在太平军拿下南京的那天,向荣追到了安庆。紧接着,第二天,琦善也跑到了安庆。他俩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夹着长江一路往东,按照咸丰皇帝的命令,打算要把天京给抢回来。

向荣指挥着一万多兵马,火速赶往长江南岸,扎营在天京城东边的孝陵卫,人们称这个营地叫江南大营。
琦善指挥了一万七千多人,他们沿着长江的北边一路前进,攻下了江北的浦口,接着又逼近扬州城,在城北的雷塘集和帽儿墩安下了大本营。跟他一起的还有直隶提督陈金绶和内阁学士胜保,这一大群人被人们叫做江北大营。
向荣和琦善只是咸丰特别关注并调动的人。江宁被攻陷,确实给了咸丰很大的打击。面对这种局面,他能做的也只是使出老三样:换人、增兵、拨款。
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后,咸丰帝折腾他那几招已经两年三个月了。人员调动频繁,钦差大臣也换了一拨又一拨,像是林则徐、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都上过阵,但都没啥用。要说原因,林则徐是没实战经验,其他四位嘛,也不咋地。
看来,咸丰挑人的眼光真的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调兵比起调人来,那更是没准儿。从金田起义爆发到太平天国把都城定在天京,咸丰皇帝下令调的兵数量多得吓人。根据一些统计,各省的绿营兵和八旗兵被调走了八万四千七百多人,再加上本省自己有的兵勇,总共加起来有九万七千七百多人,快赶上十万了,这还没算上各省临时招的民兵呢。
要找人就得花钱。那时候,咸丰总共拨出的军费大概有两千多万两。咸丰的日子,越过越拮据了。

就算日子过得再拮据,也得咬牙撑下去。听说江宁被太平天国占领了,咸丰皇帝急忙加大支援,差点连老本都豁出去了。
向荣和琦善的队伍,再加上之前的一些小部队,总共大约有三万人。咸丰皇帝四处张罗,全国能用的兵力,他都考虑过了。他又从福建、安徽、湖北、陕西、宁夏、绥远等地抽调了上万士兵,急匆匆地派往前线。
太平天国碰上的难题,开始一点点变大了。刚建都没多久,天京外面就围了差不多四万清兵。
咸丰皇帝就盼着这四万大军,在向荣和琦善的指挥下,能快点攻下天京,然后把它改名成江宁。
可是,向荣感觉这主意太冒险了,毕竟太平军人数至少有十万之众,咱们四万人要从他们那十万大军嘴里抢食,这不是在做白日梦嘛?
要不是太平天国有个大不了的弱点,向荣说不定早就战死沙场了。
克劳塞维茨这位西方的军事大咖说过,打仗时有两件大事儿,每个指挥官都得时刻牢记心头:第一,得把咱们的精兵强将凑一块儿;第二,得想办法把敌人的战斗力给打没了。
说白了就是,把力气往一处使,人多自然就占优势,人少就容易吃亏。就像想想街头斗殴,二十个人对五个人,哪边赢面大,不是一目了然吗?
要想打败敌人,关键是要削弱他们的战斗力,这就是说要争取打大胜仗,要么不打,打就一定得赢。话说回来,打大胜仗也不意味着非得把敌人全消灭干净,不是像古代项羽、白起那样,一次性活埋几十万人。其实,还有个更仁慈也更聪明的办法,那就是收服他们,让他们加入我们。

在集结强大兵力方面,太平军在定都天京前大都做得挺好。不过,说到打败清军、削减他们实力这块,他们做得实在太差劲了。
在广西那边,要说打得漂亮的一仗,就得提永安突围时的大桐埋伏战。这场仗啊,多少带点个人情绪,不光是军事计划。原来,乌兰泰在龙寮岭杀了太平军好几千家属,太平军为了报仇,一股脑儿地投入了这场大战。结果大桐埋伏战打得清军落花流水,四个总兵都丢了命,几千清兵也被干掉,太平军这下子进军就顺利多了。
真可惜啊,在太平天国把都城定在天京之前,他们打的大仗里,也就只有石达开在牛头洲那次,干掉了向荣的好几千人马,算是狠狠地赢了一把。除此之外,他们要么是追不上敌人,要么就是敌人跑得快,都没能把敌人彻底消灭。结果这些漏网的敌人后来都回来了,还成了攻打天京的主要力量。
#百家说史# #6月发文冲刺# #夏季图文激励计划#
胜宇配资-炒股配资官网平台-免费配资平台-重庆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